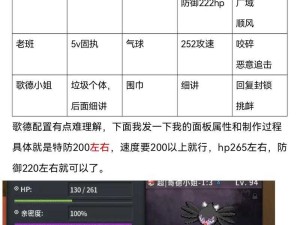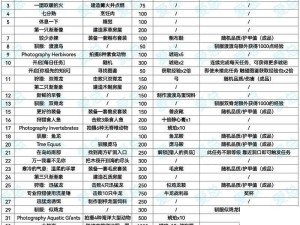禁忌的温情!和妺妺共浴时那些悄悄触碰的甜蜜时刻
热气腾腾的浴室里,她低着头搓洗后颈,银白色的泡沫顺着肩胛骨的曲线滑落。我假装擦拭背脊,指尖却不自觉擦过她脊椎上最后一片嫩粉色的胎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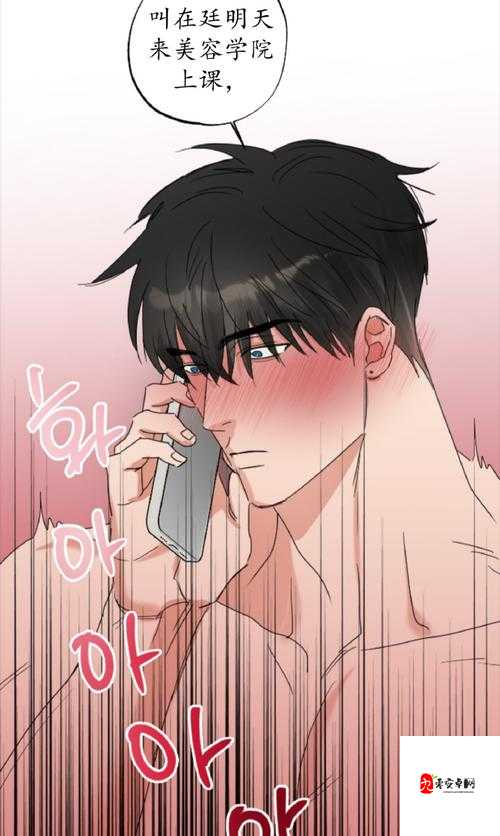
那块月牙形的印记像春日新抽的柳叶,沾着水珠的触感清冽得让人心悸。毛巾扫过腰腹时,她突然转过身,我来不及抽回的手掌正按在她还在发育的椎骨上。她僵在原地两秒后,肩膀微微颤动:"哥、你用力了..."
我们就这样僵在浴缸里,连冲洗花洒的水流都仿佛成了局外人的窃笑。她没再挪动,只是仰起脸冲我说话,湿润的发梢垂在锁骨窝,那里泛着比肩膀更浅的粉红。我感觉自己的耳垂烧起来,余光瞥见她腰间围的毛巾正露出一片月牙形的白皙。
二、那个夏天,我们都在学游泳
溪边总是热得要命。小镇人夏天都爱往水库跑,我和妹妹踩着人字拖混在孩子堆里。她总要我陪她漂浮,说不然会呛水。我就蹲在水里,让她趴在我后背上,像托着一片会出汗的丝绸。
她的拇指无意中攀上我的肩胛骨时,我们同时屏住了呼吸。水库水面晃着油亮的日光,把我们的倒影叠成一团。她突然笑起来:"哥你肌肉好硬,当沙包都不晃。"我把她转过身,假装纠正姿势,掌心却故意贴在她后腰最软的地方。
三、奶奶的蒲扇总是来得太准
去年梅雨季节,妹妹忽然发高烧。我端了温水坐在床沿,她蜷在枕头上把额头发烫得泛红。手刚伸向她的额头,她突然把我的手腕拽到颈后:"哥,帮我揉揉这里..."
我听见自己吞口水的声音。她的睫毛在枕套上投出扇形暗影,鼻翼翕动带着灼热的温度。指尖擦过喉结下方的凹陷时,门缝里漏进奶奶咳痰的声响。我慌忙缩回手,却见她已把帕子裹住自己滚烫的额头。
四、春雷总是打在不该打的地方
葬礼结束第三天,妹妹开始问我为什么每次见面都要装生疏。她说她不想当累赘,可我明明看见她在折叠骨灰盒时手指抽搐的样子。我递给她保温杯时,她忽然扣住我的手腕:"哥,你心跳和我跳得一样快..."
那是三月的雨天,油菜花田被浇得稠黄。我们并肩蹲在墓碑后,衣服都沾着泥水。我听见她擤鼻涕,听见她口袋里的硬币随着抽泣声叮当作响,听见她突然说:"我记起奶奶总是说,人到二十岁骨头才会硬..."
雨停了。妹妹说她要去采野花。我望着她单薄的背影,想起最初那道月牙形的胎记。这时候能说什么?该告诉她我也记着每道疤痕的位置吗?该说她发梢沾水时像奶奶年轻时的梨涡吗?还是该趁她转身时告诉她:我也摸过她颈窝,那里藏着春天的温度。
春雷再来时打在油菜杆上,打在墓碑上,也打在某个人犹豫不决的心头。妹妹蹲在花丛里突然大笑,说这花苞像极了去年旱灾前的霞光。我看着她的侧脸,突然想起那个被水汽模糊的上午:她转身时衣领后藏着的粉色胎记,比记忆中鲜艳了三分。